1)谷歌凭借 Gemini 3 和 Nano Banana Pro 正在走出“创新者的窘境”。更重要的是,它拥有 AI 时代最深的护城河——TPU 算力集群。在 AI 算力重心从“训练”向“推理”转移的下半场,谷歌拥有其他巨头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
2)市场低估了“推理成本”对 AI 商业模式的毁灭性打击。当竞争对手必须向英伟达缴纳“过路费”时,拥有自研 TPU 的谷歌拥有了定价权。这正是巴菲特看重的“深度价值”——低成本带来的高安全边际。
3)市场曾经担忧 AI 杀死搜索广告,但 Gemini 3 正在将搜索从“寻找链接”变为“决策引擎”。AI 带来的高意图流量有望大幅提升广告转化率(ROAS),从而支撑更高的广告单价。
4)谷歌集齐了“最强模型(Gemini 3)+ 最强算力(TPU)+ 最大入口(Android/Chrome)”。这种垂直整合让谷歌在 AI 时代拥有“全栈主权”,5 万亿市值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在美股科技巨头的牌桌上,谷歌(Alphabet)过去两年里拿的一直是一副“尴尬”的牌。自 ChatGPT 横空出世以来,谷歌仿佛陷入了“大公司魔咒”: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内部执行力被质疑。市场一度给谷歌贴上了“下一个雅虎”的标签。
然而,风向在 2025 年下半年发生了剧变。
随着新版生图模型 Nano Banana Pro 以及最新大模型 Gemini 3 的发布,全球科技圈重新感受到了来自山景城的“技术压迫感”。更令人瞩目的是,一向对科技股保持审慎的“股神”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大举建仓谷歌。
在多重利好的共振下,谷歌股价近日突破 300 美元大关,市值挺进美股前三。那个曾经统治互联网的霸主,是否已经苏醒?谷歌的下一步,会否突破 5 万亿市值?
RockFlow 投研团队认为,300 美元不是终点,而是谷歌价值重估的新起点。谷歌正处于“价值回归”与“技术爆发”的双击时刻。本文将从 TPU 的硬核逻辑、Gemini 3 的战略意义以及搜索商业模式的重构三个维度,深度解析谷歌的“反击时刻”。
核心底牌:TPU 与被忽视的“推理套利”
如果说模型是 AI 的灵魂,那么芯片就是 AI 的肉体。市场往往盯着屏幕上的 Gemini 对话框,却忽视了那个在数据中心里默默嗡嗡作响的真正胜负手——TPU(张量处理单元)。
AI 半导体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资源再分配。过去两年是“训练时代”,英伟达(NVIDIA)凭借通用性极强的 GPU 垄断了市场。但据 Brookfield 预测,到 2030 年,75% 的 AI 计算需求将集中在“推理”层(即模型响应用户提问的运行阶段)。
训练是一次性的资本支出(CapEx),而推理是持续的运营成本(OpEx)。对于 OpenAI、Meta 这样的公司来说,推理成本是巨大的负担。仅 OpenAI 预计 2024 年的推理成本就高达 23 亿美元。
但这正是谷歌 TPU 的机会。
不同于 GPU 这种为了兼顾图形渲染、科学计算而背负沉重“架构包袱”的通用芯片,TPU 是专为神经网络数学运算设计的 ASIC(专用集成电路)。它摒弃了缓存、分支预测等繁琐机制,采用独特的“脉动阵列”架构,让数据像血液一样流经芯片,大幅减少了对内存的读写次数。
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谷歌最新的 TPU v7 (Ironwood) 在每瓦性能上比上一代提升了 100%。独立基准测试表明,在优化环境下,TPU 的推理性能比英伟达 H100 高出 4 倍。
这意味着什么?当竞争对手的云业务毛利率因为购买昂贵的英伟达显卡而被压缩至 30% 时,谷歌依然可以保持 50% 以上的毛利率。
潜在的“推理套利”现在已经出现端倪:
- OpenAI 的背叛:2025 年 6 月,OpenAI 开始租赁谷歌 TPU 用于 ChatGPT 推理,这是为了降低对英伟达的依赖。
- Meta 的转向:扎克伯格正在与谷歌谈判,计划在 2027 年前部署 TPU,以降低数百亿美元的 GPU 采购成本。
- Midjourney 的证词:迁移到 TPU v4 后,推理成本降低了 65%。
谷歌的 TPU 是其未来十年云业务最大的竞争优势。它让谷歌从被动的“算力买家”变成了规则的“制定者”。在 AI 基础设施的战争中,拥有自家芯片的云厂商,才拥有最终的定价权。
Gemini 3 与 Nano Banana Pro:全栈优势的爆发
硬件的优势需要软件来释放。Gemini 3 的发布,证明了谷歌已经将其“Brain + DeepMind”的人才密度转化为了无与伦比的产品力。
Gemini 3 不仅仅是在基准测试上击败了 GPT-5.1,更重要的是它展现出的“原生多模态”能力。它不是文本模型外挂一个视觉编码器,而是从训练之初就“看见”了世界。
在长上下文窗口(Context Window)的处理上,Gemini 3 能够轻松处理数小时的视频或百万行代码,且保持逻辑连贯。这种能力让它从一个“聊天机器人”进化为了真正的“智能体(Agent)”。它可以理解屏幕截图、梳理复杂代码库、甚至跨越 YouTube 和 Workspace 进行多任务协作。
在云端之外,Nano Banana Pro 展示了谷歌在端侧 AI 上的野心。这是一款专为移动设备优化的模型,可以直接运行在 Android 手机上。
这里有着 OpenAI 无法企及的护城河——分发渠道:
- Android——全球 30 亿活跃设备
- Chrome & Search——数十亿用户的默认入口
- Workspace——数亿办公用户的日常工具

谷歌不需要像 OpenAI 那样去“获取”用户,它只需要进行一次软件更新,就能将 Gemini 3 推送到数十亿用户面前。这种“零边际成本”的分发能力,结合 TPU 的低推理成本,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飞轮:更多用户 -> 更多数据 -> 更好的模型 -> 更低的成本。
巴菲特的逻辑:当“价值投资”遇见“AI 革命”
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建仓,为谷歌的 4 万亿之路提供了最坚实的背书。为什么一向回避科技股(除了苹果)的巴菲特会买入谷歌?
在 AI 泡沫论甚嚣尘上时,谷歌的 PE 仅为 27 倍左右,显得独树一帜。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谷歌提供了一种完美的“非对称收益”:
- 下行风险有限:即使 AI 是一场泡沫,谷歌依然拥有全球最赚钱的搜索广告业务,这是一台每年产生数千亿自由现金流的印钞机。
- 上行空间巨大:如果 AI 是未来,谷歌凭借 TPU 和 Gemini,将是基础设施和应用层的双重赢家。
巴菲特钟爱苹果的原因之一是其疯狂的回购。谷歌正在变得越来越像苹果。利用其庞大的现金储备,谷歌持续回购注销流通股,直接提升每股收益(EPS)。这种确定性的股东回报,在动荡的科技股中显得尤为珍贵。
商业模式的重构:AI 会杀死搜索吗?
数年以来,压制谷歌股价上涨的最大障碍,是市场对“搜索已死”的担忧。如果用户直接问 AI 要答案,谷歌的广告位往哪放?
确实,传统的搜索模式正在受到挑战,AI 直接给出答案可能会减少用户的点击次数。但 RockFlow 投研团队认为,对谷歌而言,AI 实际上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从“流量分发”转向“高价值决策”。
以 Meta 转型移动端为例:2012 年 IPO 时,市场担心手机屏幕太小放不下广告。结果 Meta 发现,虽然广告数量减少了,但移动端的信息流广告更精准、点击率更高,最终支撑了更高的广告单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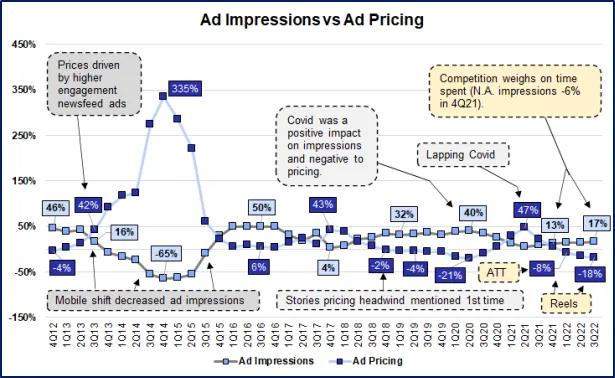
Gemini 驱动的 SGE(生成式搜索体验) 正在经历类似的逻辑。当用户询问“哪款跑鞋最适合马拉松”时,Gemini 不再只给链接,而是直接结构化地对比不同鞋款的优劣。这种“高意图”的搜索场景,其广告价值远高于传统的关键词搜索。
只要谷歌能够证明,AI 辅助下的广告转化率(ROAS)更高,广告商就会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搜索并未死去,它只是在进化。
结论
回顾科技史,每一次平台级变革,都会诞生新的王者。思科赢在互联网基建,苹果赢在移动终端。
而在 AI 时代,谷歌是唯一一家拥有“全栈主权”的公司:
- 芯片层:TPU 让其摆脱英伟达的“税收”,拥有最低的推理成本
- 模型层:Gemini 3 帮助夺回大模型之战的胜利
- 入口层:Android 和 Chrome 提供数十亿用户的默认接入点
- 资金层:搜索业务供给近乎无限的研发弹药
微软和 OpenAI 是强强联合,但存在整合摩擦;Meta 是开源破坏者,但缺乏芯片硬件和生态配合。唯有谷歌,将这四层能力完美内化。
谷歌股价突破 300 美元,不仅是估值的修复,更是市场对其“AI 基础设施之王”地位的确认。通往 5 万亿市值的道路并不需要奇迹,只需要谷歌继续坚定执行——用 TPU 守住成本底线,用 Gemini 拓展应用上限。
对投资者而言,现在的谷歌,或许正处于过去十年中性价比最高的击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