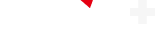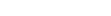读完麦克斯·班尼特的《智能简史:进化、AI与人脑的突破》(下简称《智能简史》),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撼。长期以来,我一直被本专业中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困扰。这说明我的认知结构里存在重要的缺口。这本书并没有完美地填补这些缺口,其实也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做到,但它确实让我在继续思考这些问题时,获得了全新的视角。
这本书初看起来和经济学、管理学没有什么关系。它是关于智能的,而且主要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的智能,或者说人脑智能。更准确地说,它讨论的是人类智能的演进历程。
一个经济学家的困惑
我的主业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不同个人组成的社会。因此,和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对人类行为规律的研究构成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经济学研究个人行为的时候,通常都采用理性人假设。这个研究范式的基本框架很简单:第一,将人的行为等同于选择,即有意识地决策;第二,将选择假设为“理性”的,每个人都像精于计算的机器人,能够精准地识别外部约束条件,找到让自己偏好最大化的选项;第三,将个人的偏好假设成是“稳定的”,不会改变,也无实质差异。
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助于推动经济学朝着经验科学的方向前进。人的行为是可观察的,约束条件也是可以观察的,而人的主观偏好或者说价值观是难以观察的。如果将主观偏好视作可以改变或者因人而异的,那么任何行为都可以用偏好的变化或者差异来解释。比方说,有人实施损害他人的行为,可以解释为这个人偏好以看到他人受苦为乐,而有人采取利他的行为,则可以解释为这个人的偏好是助人为乐。这样一来,什么行为都可以解释,也就意味着什么行为都得不到科学意义上的解释。
毫不意外,这一研究范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众多批评者中,就包括那本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长盛不衰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的作者、以天才自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
演化论的辩护与困境
无论这些批评如何尖锐,时至今日,经济学分析人类行为的主流范式,仍然以理性选择模型为基础。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而有力的辩护,由阿兰·阿尔钦(Armen Alchian)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分别给出。
这两篇被认为是奠定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研究方式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文,大致思想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稀缺世界中的资源配置及其效率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由多人组成的社会而言,资源的稀缺都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竞争无日无之,而任何非理性的行为都会在这样的竞争当中被淘汰,尽管他们很可能只是凭惯例或直觉行事,根本没想过自己的行为与经济学里的模型有什么关联。
这就好比台球高手往往不是物理学家,但是他们的击球动作一定会表现得好像他们总是在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就会被竞争所淘汰。更有冲击力的例子是,虽然天上的飞鸟并不掌握空气动力学,但它们的飞行姿态和轨迹一定能够由空气动力学模型接近完美地模拟。
这样的视角显然带有鲜明的现代生物学特征。更准确地说,这是借鉴了进化论的视角。举个例子,工业革命之前,伦敦的蛾子外表颜色较浅,而工业革命导致伦敦下风区工业污染加重,于是外表颜色更深的蛾子在种群中取得优势。进化论的解释是,蛾子的基因在代际之间既有遗传又有变异,变异是完全随机的,没有方向,比方说在体表颜色这个维度上,可能变深也可能变浅,甚至可能变成红色、蓝色或者绿色,但只有和被污染的环境颜色接近的基因才有可能幸存下来,而其他颜色都会因为更容易被鸟儿发现而淘汰掉。在这个解释中,每个具体的蛾子或者基因的生物学和化学细节并不重要。
虽然经济学家的辩护相当成功,但是将现实当中丰富多彩的人类行为通通简化为一个利益最大化的计算程序,在很多方面都让人意犹未尽。一点直接的遗憾是,很多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非常重要的现象,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是缺位的。在由理性人组成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算无遗策。他们永远不会出错,没有朋友,没有情感,没有想象力。直觉、判断力、意志品质、个性……全都没有存在的价值。这样的生活太枯燥乏味了。不妨说,这是一个纯粹由AI组成的世界,跟活生生的人类没什么关系。
行为经济学的反击:“不服周”
于是有了行为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颇有点周代楚国的派头——“以蛮夷自居”。武王伐纣,周代商而立。南方的楚国先祖本是颛顼后裔,却只封了个子爵。后来楚国国力日盛,遂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好比说,我不过是蛮夷而已,够不着和你们文化人玩,干脆自己另搞一套好了。这是赤裸裸地挑战周礼和周天子权威。再到后来,楚庄王陈兵周境,“问鼎之轻重”,更是要倒反天罡了。时至今日,两湖地区仍有方言“不服周”之语。
行为经济学一开始就以主流经济学的异议者自居。它挑战的关键对象,就是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家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大量行为并非出自理性选择,事实上直觉、本能、情绪等非理性因素都在人的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本质上是一位杰出的职业心理学家。他的科普著作《思考,快与慢》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优秀入门读物。这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将人类的认知模式区分为“系统1”和“系统2”。
其中系统1是自动触发的,依靠直觉和情绪,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下意识”或者“无意识”。它反应快,速度可以达到毫秒级,但与有意识的意志力和理性思考关系不大。正是靠着这套系统,我们的祖先才得以在危机四伏的大自然中幸存下来。系统2则与理性思考相关。它运算速度比系统1慢得多,但优势是逻辑性更强,因此更擅长处理复杂问题和进行深度分析,比方说计算86×73、为去阿勒泰旅游三天做攻略、下围棋、做理综题等。
但总体而言,系统1对人类决策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但它的重要性常常被严重低估了。一个有些反直觉的事实是,现代人95%以上的行为都由系统1驱动。想一想那些影响你人生的重大决策,比如和谁谈恋爱、高考志愿怎么填、在哪个城市工作、去哪家企业上班、和谁共度余生……是不是大部分都是“拍脑袋”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斯密到凯恩斯:情感的本能
行为经济学和所谓主流经济学之间的鸿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恰恰相反,在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两者圆融无碍。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就将行为经济学的源头上溯至斯密。
其实在斯密的世界里,人从来就不是完全理性的。恰恰相反,他极其重视情感对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作用。事实上,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道德情感论》。尽管后世尤其是经济学家将斯密的《国富论》奉为圭臬,但斯密本人更看重的,却是这本《道德情感论》,因为这本书系统地说明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人类何以组成社会?
附带提一下,这本书在国内常被译作《道德情操论》,这是容易引起误解的。道德和情操两个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是高度重叠的,都指向正向的伦理目标,但斯密的重点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组成社会,根源在于人性深处存在着非理性的情感,并且不同人之间会产生情感的共鸣,这就是所谓“同情心”或者说“同情共感”的能力。
这种同情共感首先意味着人们设身处地或者说换位思考,以体验对方处境和情感的能力。看到自己喜欢的球员如姆巴佩或者亚马尔起脚射门,如果足球应声入网,我们可能会和射手一样激动,甚至忍不住跳起来挥拳庆祝。而如果因为差之毫厘只击中门框,我们也会和球员一样痛感惋惜,甚至仰天长叹。
从思想史角度看,强调非理性作用的大经济学家并不只有斯密。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样认为,情感和情绪是理解人类行为与市场规律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几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合著了《动物精神》,系统阐释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在凯恩斯理论中,“动物精神”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源自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驱使人们为未来可能的成功下注,即进行投资。它是非理性的,类似于尼采提出的“强力意志”,或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
不确定性:连接一切的关键
非理性因素对于个人选择、经济运作和社会发展为什么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复杂多变。与之相比,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不确定性就源自两者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根据人们对事物的认知状态,现代经济学家将事物分为三类:第一,事前就知道准确结果的确定性事件;第二,事前不知道准确结果,但知道其概率分布的风险事件;第三,连概率分布也不知道的不确定性事件。
如果世界是完全确定的,经济系统的运作就变得非常简单:这意味着人类无所不知,不会出错。这时候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完全有效的。
如果世界除了确定性就是概率分布已知的风险,经济系统的运作会复杂一点,但也不会复杂太多,无非是加上可以分摊风险的保险机制。
麻烦就麻烦在世界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不确定的程度可能远超人们日常的理解。极少有人能够在2019年准确地预言接下来会有三年疫情,或者在2022年初想到俄乌关系会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我们很难提前预见在信息化的道路上做显卡的英伟达会悄然崛起,也不知道人工智能未来会走向何方。
但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不意味着世界的运作没有规律。现在地球上形形色色精彩纷呈的生命体,都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一步步逐渐演化而来的。最惊奇的是,在这个演化过程中,产生了人类这样的高智能生物,他们会反思自己的高智能是怎么来的,并且还试图运用自己的智能来创造新的智能存在方式——人工智能。那么,如何理解这一切呢?
《智能简史》:一部进击的演化史诗
于是就有必要说回这本书,麦克斯·班尼特写的《智能简史》。
人类是很容易骄傲的物种。的确,人类有丰富的情感也有高度发达的理性,两者的结合让人类最终在地球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很多时候人类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尤其是现代人。工业革命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最辉煌的变革。但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与从辐射对称动物向两侧对称动物跃迁这一演化过程相比,工业革命就黯然失色了。
辐射对称动物是演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代动物。所谓辐射对称,指的是身体的各部分围绕一个中心轴呈辐射状对称,没有前后左右之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比如海星、海胆、水母和珊瑚虫。
在5.5亿年前,第一只两侧对称动物出现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动物物种都是两侧对称的。为什么动物的身体结构从辐射对称转变为两侧对称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呢?因为这个转变为生物史上大脑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也就为智能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辐射对称动物的身体结构能够很好地适应被动的等待食物策略,但如果要主动寻找食物,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从捕食的角度看,辐射对称结构的生物,就不仅需要有能朝各个方向检测食物位置的感觉机制,而且需要能够朝各个方向移动的运动机制。而两侧对称的身体结构对运动机制的要求简单得多,只需要能够做向前和转向两个动作就行。这种机制也让试错和及时调整成为可能。事实上,今天人类制造的几乎所有导航机器,比如汽车、轮船、飞机等,都是两侧对称的。
两侧对称结构简化了运动机制,同时对感觉和反应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神经系统进化到可以对周围不同事物做出“好”与“坏”的评价,或者说可以对周遭事物的效价进行编码,并且形成能够将多个输入信号整合成单个转向决策的大脑,能够基于自身状态调节对这些评价的反应,一个“理性人”的雏形就出现了。与此同时,两侧对称动物体内还产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神经递质,比如多巴胺和血清素,它们让关联性学习成为可能。也正因为这些神经递质的出现,这些看似简单的大脑就已经能够调节各种刺激的相对效价,并且产生四种基础性的情感原型:快乐、痛苦、满足和压力。
以上这些知识在班尼特这本书里得到了清晰而生动的介绍。不仅如此,班尼特还生动展示了学习的演化和本质,以及与此相关的时间感、好奇心、恐惧、兴奋和宽慰等一系列智力和情感要素的形成过程。
此后,现代新皮质的出现让大脑的功能更进一步:能够通过想象来学习,于是模拟和规划的能力诞生了。在物种演化史上,这对应的是灵长类出现之前的小型哺乳动物。而在新皮质中演化出能够建立思维模型的新区域之后,灵长类就出现了。它们能够利用思维模型来预测自己未来的需求,理解同类的意图和认知,并且通过观察来学习新技能。
接下来的战略性突破则是语言。语言的出现将不同个体的认知联系起来,在语言交流中,不同的思想得以碰撞和融合,在产生新知识的同时,也使得知识能够跨越代际不断积累。人类出现了。
智能的本质:在不确定中进击
上述知识以这种方式讲述出来,是非常有趣的。不仅如此,而且我相信,即使对于专家而言,无论是生物学家、人工智能专家,还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如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都是相当新奇的。
对我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是从人工智能和生物演化双重角度,生动地还原了大脑或者人类智能一步步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部生物与不确定的环境相爱相杀的历史。
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稀缺,另一个则是不确定性。两个概念描述的都不是客观世界的内在属性,而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描述人类主观欲望和外在世界的关系,后者则描述主观认知能力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从稀缺这一前提出发的探索已经非常丰富了,但以不确定性为支点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理解不确定世界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演化是非常重要的视角。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无论对于经管领域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或者任何对人类的行为、情感或者社会运作感兴趣的人士,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优秀作品。